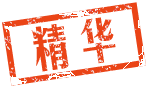我叫若希,若希的若,若希的希。二十岁,双鱼座。我习惯这么开头。
我有个很好的习惯,每个阳光明媚的早晨,用清水浸湿头发,把头发放下来,遮住眼睛。透过头发的细缝打量世界。安安说我是个忧伤的孩子,她不喜欢看到阳光照不到我的脸上。我很认真的告诉她,我需要学会,不在阳光下流泪。然后我看到安安流下眼泪。
我喜欢光脚穿大号鞋子,肥大的裤子,风可以从裤筒中贴着皮肤掠过,干燥而舒服。喜欢躲在半黑暗的房间里关着灯对着电脑读小说,文字从脑中呈现出一段段场景,真实而感动。喜欢在夜深人静的凌晨,关紧窗子,播放音乐,坐在电脑前手指熟练的敲字,习惯而享受。当这些喜欢都成为习惯的时候,这种无法形容的美感就会顺其自然,懒得去改变。
二零零四年,安妮出了新书,《二三事》。我很喜欢这个名字,就像每经过一个城市,就会经历几件事。就像安妮写的“每次写一本小说,最先出现在脑海里的,不是文字,而是意象”。每离开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,脑海里亦不是出现即将到达的城市的景象,而是在回想离开城市的经历。安安在我离开的时候对我说,那是在回忆城市遗留的伤痛。
二零零四年,我二十岁,离开沈阳,来到广州。租住的房子十坪大小,亦是半黑暗的房间,对面住着和我一样年纪的外地男女,每天深夜的时候发出床与地面敲击的声音。我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,看着幽幽暗光的镜子中反射出模糊的身型,这个时候,总会想起安安和我说的“很多时候,镜子再明亮清澈,我们都依旧无法看清楚自己”,然后对着镜子黯然落泪。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了三个月。
我继续放任自己的生活,正如零三年的玩世不恭,CD机里一直反复的播着安安给我的第一首歌,歌词里唱着:陪着我一直到世界的尽头,其实无需承诺……
我决定搬家,搬离那个晚上让我无法入睡的房间。第二天,我把头发染了,染成了浅浅地天蓝色,洗手间里我站在镜子前,想象自己第一次染发回家父母吃惊的表情,发现脸上的表情仿佛在笑。阳光从窗子的缝隙中透进来,我把湿漉漉的头发放下来,看着窗外的世界,阳光懒阳阳的撒在脸上,舒服的笑着。
三个月,我已经习惯了这个城市,第一次和小宇去沿江路的酒吧时,星佑坐在一边看着频繁吸烟的我,眼神非常好奇。我走过去,坐下来,熄灭手中的烟,望着她,没说话。一个月后,我知道这个漂亮的女孩叫星佑,十八岁。星佑认真的对我说,我在北方长大,十七岁以前;十七岁以后,我来到广州。我望着眼睛闪光的安安,嘴里喃喃说,可怜的孩子。星佑停止了频繁颤动的右手,我并不是孩子,十七岁之后就不是。我已经适应这个城市,这是一个阳光充沛,人潮涌动的城市,空气新鲜而干燥,高楼寂静,天空清澈。我望着她,说不出话,我知道,我开始喜欢她。
我的生活开始矛盾和改变,开始住进空气清新,阳光充足的房间;开始拒绝和陌生人聊天;开始戒掉吸了两年的中南海。睡梦里星佑安静的对着我笑,转身看到安安,对我说,若希你爱我么?我就忽然从梦里惊醒了。安安打电话过来,叙述着她的生活,我在电话一边宁静的听着。安安说,她在专业课上睡着了,老师批评了她的设计;她说她的老师是个年轻喜欢穿耐克休闲男人;她说她觉得这个男人很可爱;她说老师批评她的时候脸上都是关心的表情;她说老师打电话找不到她的时候以为她在约会;最后,她说,我的老师喜欢我。我简单的回应了一声,心里像破玻璃碎了一地。忽然想,三十岁的时候还会不会嚼着口香糖站在阳光下对着安安喊,老婆。
挂掉电话,开始失眠,转身在柜子上拿出准备好的药片,放进嘴里发出咔嚓喀嚓的声音,我喜欢这声音,可以让我有个好梦。
六月,经常看到星佑步行从上班的地方回到住的地方,楼下有个小烧烤店,有间小型电影院。每个周末我都会出现在这里,等星佑下班,晚上十点中的时候,星佑出现,我笑着对她说,来喝雪碧吧。然后见她上楼再下楼。等到周三她休息的时候,我会买两罐雪碧陪她去那间小影院去看电影。从那以后,我可以看见星佑脸上开始多了笑容。
杰伦出了新专辑,《七里香》。我还在感受这个名字的时候,CD机里已经开始播放,那个男人在唱:窗外的麻雀,在电线杆上多嘴。你说这一句,很有夏天的感觉。安安打电话过来的时候,音乐还在反复的播放,安安在电话那边咯咯的笑,我透过垂下来的头发缝隙看着窗外的蓝天,快七月了。
小宇说要辞去工作回北方,工作太累承受不住压力。我们笑着聊天,我说,回去到我家看看。他说,好。然后盯着我一直不说话。我说,怎么了?他沉默了片刻问我,你是不是喜欢星佑?我没回答,只是说,她太寂寞了。一个星期后,小宇回了北方。候车大厅小宇问我,安安和星佑你喜欢哪一个?我开了手中的雪碧,望着周围人看着我渐渐失去浅浅天蓝色的头发,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七月,工作开始忙,最后一次在烧烤店看见星佑,我对她说,星佑,要快乐。然后离开。同时,安安电话里和我说,学习紧张,不会经常联系我。忽然就感觉身体像虚脱的弓。
生活开始进入紧张阶段,早上九点上班,十一点回家。整整持续了一个月,七月的最后一天,忽然想,很久没有打电话回家了。于是找到一间电话吧,电话里,我对母亲说,戒烟了,过年才回家。父亲接过电话嘱咐了几句,忽然感觉父亲的声音又苍老了。挂上电话,走在街上,眼泪忽然掉下来,顺着脸颊被火辣辣的阳光蒸发。
八月,去书店买了好多书,都是灰色封面的小说。封面上写着:生命是一种游走的方式。仿佛让我想起去年大连的生活,频繁的抽烟,寂寞而孤独,反复的用烟头落在伤痕累累的脚踝上,散发着阵阵烧焦的味道。夜里反复的翻着书页,翻一页,又翻回来,往往在看完一页的时候又不记得看过的内容。就这样挣扎了好久,想说话,找不到倾诉的人。小宇在东北,纯去了厦门,星佑开始恋爱,安安不在。人们都很好。我开始怀念曾经自由的生活。
星佑第一次打电话过来,电话里,沉默了好久终于开口,若希,谢谢你,我很开心,也很幸福。我在电话一边安慰说,开心就好。然后对她笑出声,星佑也笑。我对着电话说,再见。星佑也说,再见。我说,星佑,再见。星佑说,若希,再见。挂掉电话,也许,我们永远不会在见面。
九月三日,离安安的生日还有两个月。我开始计算着准备生日礼物。我开始想,我爱不爱安安,安安爱不爱我。开始听已经停止了两个月的歌。下班的时候,安安打电话过来。电话里暖暖的喊着,若希。然后开始笑。接着电脑里唱着:窗外的麻雀,在电线杆上多嘴。你说这一句,很有夏天的感觉。手中的铅笔,在纸上来来回回,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。
这个夏天终于快要过去了。
|
|
|
我听到你在唱歌,就在我面前,但我始终走不到你身边。
|
|
|
|
|
|
|